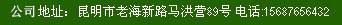|
年12月20日晚19:00,费孝通先生的“书童”张冠生老师做客第期「松社我来讲」从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八十周年说起,与现场读者分享费先生朴实专注的一生。 首先为大家放上一段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一段感慨: 冯唐易老,弹指间已是一个花甲了。我自己固然须眉皆白,养育我的家乡如今却更年轻庄健了。流年似水,原是一般人都易生的感叹,但不知自从世界上有了人,人一代代地劳动生产,把时间变成了积累的基础。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怕时间的冲洗了。 本期「松社我来讲」的讲课方式与之前略为不同,方式新颖却更能抓住现场读者的心,张冠生老师采用PPT——费孝通先生称其为“讲义的旁白”(围绕新书《探寻一个好社会》的旁白),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现将张老师的讲演整理如下,望能弥补各位未曾到场或已到场却来不及记录的读者朋友的遗憾。 费孝通先生的讲课习惯,一般是在课前为大家提供讲义,讲课过程中不对讲义内容进行重复,只讲字里行间的内涵,叫做“旁白”。所以,听费先生讲课的学生、老师、普通民众等都会收获至少双倍的信息量。费老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珍贵的,其中也包括这种授课方式。 在第期「松社我来讲」的讲坛上,张冠生老师沿用了该授课方式,也受到了现场读者朋友的喜爱,这也算是对费老先生的一种敬意吧。 在前两天的松社预告中,相信大家对费孝通先生和张老师有了些许了解,在此不做展开介绍。张老师现场准备的PPT内容丰富,生动地向我们呈现了费先生作为“一生超前”一位学者为中国人类学的学术研究默默奉献的一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想着要努力多做一些人类学研究,多为后代留下丰富资料,这种精神让现场读者们不自觉地生出一份敬佩和感动。 据张老师概括,费先生的学术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年——年是第一次学术生命,主要著述有《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民主宪法人权》等等。年——年是其学术研究空白期,但这段时间费先生依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如“留英记”、“干校家书”、印度资料翻译、《世界史纲》的翻译、检查认罪材料等等;年——年是费先生的“第二次学术生命”阶段,主要著述有《小城镇四记》、《社会调查自白》、《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逝者如斯》、《从实求知录》等著作。 一、弃医从文和第一次学术生命阶段 张老师回顾,费先生在弃医从文前,也就是二十岁之前,写了很多文艺评论文章,已是高水准著作,有条件往文学方向发展。但用费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在上大学时,先是想当个医生,好为人治病,免除人们的痛苦,于是我进了医预科。后来我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于是我改学社会学,……来认识社会,然后改革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年,费先生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在此结识影响其一生的老师吴文藻。年毕业后,吴文藻老师带着费孝通来到清华大学,师从人类学教授史禄国,费先生因此成为当时清华大学研读人类学的唯一学生,踏上“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的人类学研究道路。对这段学业时光,费先生这样说道,“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追念中不时感到这段生活似乎和我的一生中的基调很不调和,甚至有时觉得,似乎是我此生不应当有的一段无忧无虑、心无创伤的日子。这些日子已成了一去不能复返和我一生经历不协调的插曲了。”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到,费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怎样度过的,而费先生也正是在这段“无忧无虑、心无创伤”的日子里完成了从医人到医国的思想转变。 年,费先生从广西省入手,做了瑶山调查,他自己也说“自愿要做个发展中国人文学科的探路人”。在瑶山调查期间,发生了惨烈事故,费先生失去了他的新婚妻子王同惠,为此曾想与亡妻同生同死。但求死未果,“好像进了一个永远都打不醒的噩梦”。既然寻死不得,“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即“愿意用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要在二十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 年夏,费先生为养伤回到家乡江苏吴江。费先生的姐姐费达生曾是江苏省立女子蚕校的一名教师,于年1月5日与其丈夫,也就是该校校长郑辟疆一起帮助农民成立了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机械丝厂。费先生曾说,自己的姐姐有可能是中国乡村企业第一人。费先生的姐姐建议费先生到江村养伤,这才有了江村调查。费先生在晚年时回忆往事,曾感慨道,“我觉得我自己的一生都是在跟着我的姐姐走,她在前面做事,我讲出来她做事的意义,可是我总也赶不上我的姐姐。” 费先生在江村做调查时,深刻感受到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农耕文明将要因为现代工业机器的介入,而发生一场深刻的文化变迁,油然生出要对江村进行细致研究的浓厚兴趣。在他当年写的《江村通信》一文中,主张对人类学眼界方向进行革新。张老师认为这段文字放在现在来看,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中这样阐述道“社会研究不比其他一定有收获量的工作,而且从工作开始到完成又不能有一定的时间。若是一个研究者在有一定限制的时间中,一定要编写报告,诚实的,不能详细校核得到的材料,出版不成熟的作品;不诚实的,不能不牵强事实,或甚至制造事实,写成于社会研究有害的东西。一个实地研究者最好不负‘报告’的责任,使他能够根据兴趣去获得充分的认识,等到所认识的已有了系统,有了可‘报告’的时候,才编写他的报告。”同时,费先生的“江村调查”是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是完全个人性质的调查,没有课题经费的支持,也没有向任何单位申报课题。 随后,费先生带着他的调查资料到了伦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向伦敦经济学院写了推荐信。自此,费先生跟随国际人类学界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了博士研究学术生涯。张老师解释说,从国际人类学研究进程来看,曾有过三个不同阶段。第一段,“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在做研究,凭借的是探险家、外交官、传教士等提供的资料。第二段,是人类学家走出书斋,进入到实际生活中,成为田野里的人类学家,自己拿到了第一手资料。到马林诺夫斯基领衔国际人类学研究的时候,他逐渐感到人类学需要又一次转折,即由对“化外之地”对研究转向对文明社会的研究。至于在什么时候、谁来完成此次转折,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并不十分清楚。正在此时,他看到里费先生的江村调查素材,眼前一亮,他期待、瞩望的这次转折,将要由他的学生费孝通来完成。 在马林诺夫斯基悉心指导下,费先生于年完成其博士论文,人类学界第一次有人依据翔实的人类学调查资料,向世界讲述中国农民的故事。马林诺夫斯基写下这么一段话对费先生完成的这次转折做了肯定: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费先生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立刻赶往云南昆明,参加吴文藻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在呈贡魁阁成立一个小小的研究班子,称社会学研究室。学界有人称,这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雏形。年--年,费先生在云南主要实地考察了禄村(禄丰县)、易村(易门县)、玉村(玉溪县)——“云南三村”。费先生是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在回国后如此迫不及待地参加到云南乡村调查研究中去的: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同时,20世纪40年代,费先生和他的同事、学生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学者集团,他们出版了大量书籍供后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费先生这样说起那段时光:“以客观形势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 张老师介绍,这个时期,费先生的研究由个案向类型过渡,又由类型向通论过渡,出版了《乡土重建》、《乡土中国》、《乡村社会学》、《生育制度》、《民主宪法人权》、《中国绅士》等著作,也进入了他的治学丰收期。《乡土中国》初版时印行三千本,一个月内售罄,此后半年,每月加印平均本。随后,张冠生老师简要介绍了费先生这段时期的著作,让现场读者对费先生的治学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年6月,费先生作为中国十教授之一接受美国的邀请,进行学术访问和文化交流,朋友也建议费先生趁此机会“休息休息,养养胖,回来再干”,可是费先生此时“心中总是沉着一块丢不掉的石头,时刻担心这地球背面那四万万人的前途”。同时,在美国进行交流时也生出了很多感慨,如“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的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这光明又是否全盘西,或是全盘东?这又会成什么东西?”(摘自《初访美国》) 这一时期,也越来越接近政权更迭的年代,费先生曾说:“我们对共产党人有积极印象,他们爱国又能吃苦,我们逐渐把他们看作振兴中国的力量。我相信和共产党人可以一起工作。我们的确一起努力使大学运转,避免紊乱……我们完全没有摩擦。”自此可以看出费先生对中共的态度,同时,费先生于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自由知识分子政治联盟。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费先生对一切都保有着满腔的希望,费先生在解放过程中“学到很多根本性的、很宝贵的经验,并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年,费先生将之前写的散落的文章重新编辑汇总成《山水·人物》,他在题记中写道:局面变得真快,很可能作者已代表了一个抛在时代后面的人物。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的进行、三大改造的完成、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等等的时代变化,费孝通先生终于能有机会在年4月26日至5月16日,重访江村20天,“每天晚上要用掉一斤灯油”,可见当时费先生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情况依然满怀激情和热切。 二、学术空白时期 年,费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失去了继续从市学术研究的条件。据统计,费先生第一次学术生涯中共留下将近万字著述。在其学术空白时期的二十多年里,留下了38万字的文字资料。费孝通说:“经过‘反右’和‘文革’,知识分子伤到骨子里了。”但“伤到骨子里”的费先生依然昆明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比较好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就业即日起2016甘肃省考笔试成绩在
- 下一篇文章: 公务员涨工资最新消息6省份公务员基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