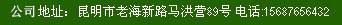|
可能是造物主的吝啬,仅给了这里一片贫瘠的土地;也可能是造物主的偏爱,给了这里一群与众不同的会宁人。生活在这里的人,由于自然条件的刻薄,命运注定了他们拼搏的一生…… 如果把甘肃看成一个斜挂着的两头大的糖葫芦的话,会宁就是下边那颗最涩的一块。祖国大西北的甘肃向来以既“干”又“酥”而著称,会宁便是这干苦浓缩的精华。每年到了三四月,缺水就成为困绕会宁农民的一大难题,就像灾年的粮食青黄不接一样,家家在每一年六七月份收集在窑里的那一点水到了两年的交接处都已捉襟见肘了,而天却迟迟不下雨,农民的心就像土地一样开始干焦。如果村子前后有一口有水的井,就成了全村人的“命根子”。我们村就有一口,在村子中间,人们都叫它“老井”,不知道它有多老,自从我记事起,人们就这样叫它了。老井里的水很甜、很凉,我们都爱喝,不煮喝了肚子也不痛。老井的水也大,听老人说是过水,也许是吧,舀干时候不大就又能蓄一尺深。但是,能得到大自然这样恩赐的村庄毕竟太少了,很多村子就根本挖不出一口有水的井,像草滩、新源、四方等,地下几乎没有水。怎么办?那可惨了,除了到外地买水外就只有不惜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到邻近的村子去“借水”了!借了当然是不可能还的了。到了缺水的季节,为了大家都能喝到一点水,我们村的老井也就临时上锁了,每天中午和傍晚各开一次。开井时刻到井滩去,可热闹了,比赶集的人还多--本村的、外村的,男女老少都有,牛羊等牲口也在人群中来去穿梭。那几十里路赶来的外村人,为了多带走一点水,大多几乎全家出动,有挑桶的、有拿塑料壶的、有提大铝壶的,还有的小孩拿着塑料瓶;有肩挑的,有牲口驮的、有架子车拉的。看着他们顶着正午的烈日,挑着两桶水一步三晃的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怕洒出一滴水而提心吊胆的情景,不由使人惊叹万分。但即使他们半点水也别撒,走回家也只剩两半桶了,别的水呢?在路上喝了。 会宁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一碗油换不来一碗水。”道出了这里水的珍贵。如果你走进会宁农村的每个家庭,都会在厨房里发现一个一米多高的大缸,是装水的,挑来的水全部装在里面,慢慢地用,一点点地用,能省的尽量省,绝不能有半点的浪费。只有他们才深深知道这水是来之不易的。在缺水的季节,半个多月不洗脸在这里已习以为常,绝不会招来惊异的目光。会宁小伙子找媳妇,姑娘家首先要问的是:“你们村子里有没有井?”如果没有,很可能这桩婚姻就告吹了。井,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决定婚姻胜负的“法宝”;井,已成为会宁人的“命根子”;井,已溶为会宁农民的一部分!会宁人对井的渴望,决不亚于城里下岗职工对一份好工作的渴望!吃水莫忘打井人。打一口井,得向地下挖三四十米,不知多少人为此流了多少汗,为此吃过多少苦,为修一口井,甚至有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大自然的十年九旱,已使会宁农民无法摆脱水的困惑,无法忘记井的甘醇。吃水已是这样的困难,农业灌溉更是不敢设想。二月种子下地后,风吹起松软的黄土,天地间整个弥漫着黄色,黄色掩盖了山坡,黄色掩盖了村庄,黄色掩盖了人……走上了乡间的小路,路面整个被细腻的像流水一样的黄土遮盖着,一脚踩下去,整个脚都淹没了。偶尔有一辆三轮车驶过,看着直冲云霄的黄土,不由的使人想起李白的诗句:“黄沙直上白云间。”当然,这里的不是“黄沙”,而是“黄土”,但没有半点李白那夸张的意思。老农扬起同黄土一色的脸,长叹一声:“老天爷又要减人了。”要是碰上个风调雨顺的岁月会宁亩产平均能达到三百斤已是相当不错了,但别的农业区,即使在灾年亩产在四百斤以上。这就是会宁人生存的土地,这就是会宁人赖以生存的环境!造物主赐予以会宁人的实在太少、太少了,只给了这里一片贫瘠的黄色和一片苍凉。 为了生存,会宁人不得不同环境拼命,不得不同命运抗挣,不得不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会宁人身上洋溢着中国标准式农民的朴实和厚道的气息。他们世代以农为业。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土地。远处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抓起一把黄土凑到眼前,仔细地观察,然后用鼻子闻闻、舌头舔舔,他是要搞清楚这块地里究竟缺少什么肥料。他们日未出而作,日落而未息,以近乎原始的工具一天不缺地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挥汗如雨。会宁人叫这是“背日头下西山”。每天看着那一轮火红的太阳缓缓地沉到西山背后,拣起被汗水浸透的汗衫搭在身上,收起工具,长舒一口气,拖起沉重的步子,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神情,向家里走去。 会宁多以小麦为主要农作物,不种冬麦而种春麦,少则十几亩,多则几十亩。自从二月种子下地,会宁农民就得天天上地了。打土疙瘩、松土,都得仔仔细细的过,还要时不时的扒开土看看种子是不是发芽了,是不是烂籽了,是不是窑籽了。如果是,就得及时补种。麦苗出土以后,农民更是离不开土地了,锄草、捡苗,这是农活的重要环节,一般要三遍,多则四遍五遍,锄完这块锄那块,锄完阳山锄阴山,期间还要抢墒种一些秋田。来不及喘口粗气,已经到了五月,这时候麦地是绝不能进去了,麦子大放花了,是不能碰撞的。他们就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秋田中来了,秋田三遍还没有锄完,六月来了。六月头,豌豆收,再过几天是麦口。夏收到了,这是最紧张的时刻。不管是丰收还是贱收,农民都得大干一番了,庄稼汉个个练好膀子,几亩豌豆和扁豆不觉得累就拔完了。眼看着山上的麦子已是冷黄,一片连着一片。这时媒婆都不想上路,阴阳先生也无心除魔捉鬼,家家户户天不亮就上地了。六月麦子黄,过门三天的媳妇请下床。除非老弱病残,孩子都得上地,三个孩子顶个大人嘛。于是,整个村子很难找到半个闲人。会宁人收麦子是不用镰刀的,山地麦子,既短又稀,是带不住镰刀的,他们就用自己的双手,蹴在地上爬,用一种最原始最踏实的劳动方式,来收获这份生活的馈赠。天旱年的麦子,是东山一根西山一根,追都追不上,广种薄收的会宁人,就一根根地在几十亩地里捡。人常说,麦黄一夜,说黄就金黄了,庄稼汉就得拼上命、发上狠地往前赶,还是赶不上麦黄的速度,常常拔着拔着,黄透的麦子就掉颗。这干旱了几个月的天气也变得多雨,动不动就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有时还夹杂着冰雹,十几分钟,麦穗全部落地,一年的辛苦就付之东流了。所以会宁人把六月收麦叫虎口夺食,得拼命。常常在麦子黄得快时,他就晚上也不休息了。从天没亮拔到快中午时,烈日当空,握着烫手的麦子,看着眼前蒸腾的热浪,两只手不停地迅速抓拉,而两条肐蹴的腿不停的向前蹬,过不了几个来回,小腿肚子上的汗水和黄土已和成泥,像浇了一碗热汤,粘粘的、烫烫的,十分难受。两个胳臂像灌了铅一样,一把比一把拉得吃力。背上太阳晒的火辣辣痛,渗出的汗珠子像无数条虫子咬。干涩的嗓子眼呛进了泥土,像吃了一口鱼翅卡在了上面,一阵比一阵难受。头也一阵阵的发胀,觉得昏昏欲睡。然而焦急的农民并不放慢速度,一阵紧似一阵的往前赶。 和君甘肃·九曲黄河班河汇百流,九曲不回 北京治白癜风最好的专科医院北京那个医院白癜风最好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gansushengzx.com/gsxw/1406.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甘肃陇南互联网扶贫
- 下一篇文章: 甘肃天水苹果,吃的就是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