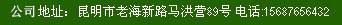|
在这闲适的夜晚,我的思路从童年走过青年直到中年,深深地感到:坚持下去才有希望,如果没有泪水与欢笑相伴,那么我永远是一个平庸的乞丐……——作者题记童年在四十年前,留下欢乐和悲辛,而记忆更多的是贫困,使我不得不想起年轻的父母和哥哥,为一家的衣食温饱艰难奋斗的身影和不可磨灭的故事,其中就有支持我读书认字的点滴情感。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家都很贫困,而处于“阶级路线”与“政治斗争”环境下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那时已经八岁的我,除了要照顾比我小五岁的弟弟外,迟上学的特殊理由是穷,穷的除了一条活着的生命依靠吃糠咽莱就一无所有了。我们弟兄五个,大哥二哥已超过了上学的年龄,因为要帮父母挣工分养家糊口,三哥上学好几年了,不堪负重的家庭却怎么也滕不出手让我早点去上学。于是我听庄间大一点孩子念书、看他们念字写字,竟然学会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文字,下雪以后还把这些字用指头写在雪上,这种字就被父亲发现了,从来不会“吹捧”儿女的父亲给一位邻居说“这个娃娃有识字能力,得赶紧让他识几个字……”,母亲听了以后,赶嫁妆一样给我缝了一个“花”书包,就是用不同颜色的旧布洗干净剪成小块又缝在一起的,没有煤油灯的夜晚母亲还乘着月光“加夜班”,这是一种除父母以外任何人达不到的辛苦和思想。记得上二年级的暑假,母亲用铲“油毫”(一种毛草,嫩芽可以入药)卖到的钱给我买回一瓶蓝墨水,让我写暑假作业;那时侯也买不起水笔,就用一种叫做“蘸笔”的笔头子用线绑在竹竹棍上蘸墨水写字,不过这种笔头子“背上”背着一个储存墨水的“囊”,蘸一次能写好多字的。一次不小心醮了墨水没有盖上墨水瓶盖撞倒了,倒得一干二净,我哭了,哭是有三个因素:一是作业没完成没有了墨水,二是怕母亲知道了骂,三是想母亲在炎炎烈日下(乘中午休息时间)铲“油毫”的艰辛(每当这个时候回家脸上流着汗)……到母亲劳动回来我还没哭罢,母亲也看到墨水倒在地上,知道我为什么哭了,就用手摸着我的头“狗娃侯(不要)哭了,妈顾你再买一瓶!”这些话让我哭的更大了(达到了嚎啕大哭的境地),第二天父亲就给我买回一瓶,笑嘻嘻的交给我。这不能再倒了,我想,就给以前的空墨水瓶里少倒了些临时写的(即使倒了还有,不至于再次倒的一干二净),把新买来的放在自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其实,让我真正重视和热爱“文化”是我上了初中。初中,我考进了会宁县四房吴乡(现在改为镇了)初级中学,“走读”路太远住校没条件(还是很穷的家庭),父亲把我转到距家最近的会宁县甘沟驿镇田岔学校,依然是“走读”。记忆中初一教语文的老师叫杨再畔(会宁韩家集人),他多次对我的作文评讲和在同学们面前朗读,大大提高了我对“语文”和“文化”学习的兴趣,教育家说过:鼓励就能够成就一个人的将来!记忆中初二教语文的老师换成杨满春(会宁四房吴人),他很有“特色”,就是每每上完课擦干净黑板,在上面默写一首唐诗或宋诗,然后夹起教案走出教室,如此这般日积月累,学过的除语文课本以外的文化更多了。那时似乎唤起了同学们读“诗”的兴趣,有的拿着《唐诗三百首》、有的拿着《宋诗三百首》、有的拿着《唐宋诗词》……很多同学只是拿着并没有读,后来我就先借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后借了一本《宋诗三百首》,在一学年里不知“天高地厚”的背下来了,那时记忆力特好,除了迅速背会语文课文,背其它课外读物有了时间也有了速度,爱好自然而然的培养成功了。我的初三是在会宁甘沟中学读的,因为甘沟的田岔中学是小学和中学合并的,初中只有到初二没有初三,听说这种“格局”的学校叫“戴帽中学”。初三教语文的老师叫孙继承,语文教的极好,感觉是个“知识丰富”的老师……初三一年是住校,缺吃少穿,到了第二学期就饿晕过好几次——每周步行十公里回家背馍馍,除了一小袋炒面就是三四个荞麦面碗脱子,而荞面碗脱子三天之内就“绿毛红胡子”的发霉了,不吃太饿、吃了肚子疼、丢了太可惜……学生灶要从家里背面去交换饭票,还要交每斤面一毛钱的加工费,既无白面可背又无钱交费,大多时侯吃炒面喝水;就是学校学生灶上的饭,中午是白开水煮白面“七花子”,一半是汤一半才是面条,没油没盐没菜,晚上是玉米面撒饭,在一口烫猪一样的大锅里,大师用一把小铁铣搅动,吃着常常遇到或干或生的面疙瘩……当我饿晕时(后来才明白吃了发霉馍馍中毒了),回家休学两个月,就再没去学校。第二年父亲又把我“插进”四房初中补习,“营养不良的后遗症”没有消除接着又是贫困不堪的营养不良,第二个学期又休学了……距离考高中只有一个月时,父亲问我:就要考高中了,再去不去学校念书了?我说:不去了!说完话猛地转过了身,因为我已泪如涌泉,但还不让父亲看到我“软弱”的泪水……这种离开学校的方式应该叫什么?叫缀学吗?叫毕业吗?叫……?是一种疼痛中的半途而废。走向社会,我想着自己的出路,一种既不花钱又能自食其力的出路,于是我便想到了入伍当兵,于是偷偷的报名了,《入伍通知书》来了,父亲不同意去,母亲更是哭得泪比河长……那就是我写过的一篇记忆诗歌《生命的自我承诺》。十八岁了就是一个“成年人”,少干活闲吃饭遭受“白眼”,无形中给父母造成压力,本来体弱力单的我一直在父母溺爱的保护伞下,但是过了不或之年的父母已无力庇护我,加之每晚看书白耗油灯第二天没有精力干农活。“包产到户”的家庭已经解决了温饱,自私的理念在每个人心里日渐加强,谁会让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看书写字不干活?后来是父亲让我去任“村委会的芝麻官——村文书”的,看是不是能“谋”出一条出路?人心不沽现实苛刻,我又不得不放弃“走向官道”的厚望外出打工谋生。然而,任何时节任何情况任何环境下都没有阻碍我读书与写作的欲望,那怕是诅咒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就在我跟着一个私人企业老板看门管理材料的四年之中,我利用每个晚上或白天闲暇,自学了中等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教师进修的卫电高师的课程,没有英语课程),迫于无钱就少了去参加一年一度的“自学考试”,倒让我学了不少“文化”。当然,这个时侯我已独立地支撑一个家庭,已经过了“四十而不惑”,是一个四个女儿的父亲,供着三个高、初中学生,责任已不允许我任性去浪费时间和钱财,生命拮据到从前饭不裹服衣不蔽体,努力挣钱才是王道,非份之想只是梦境……只是在年下半年去了白银产业园区的“白银锂盐厂”打工,突然发现一份《白银锂业报》的厂报,上班之余细细读之,觉得新鲜而又平易近人,于是就利用闲余时间写了一首长达行的诗歌《我热爱的扎布耶》交给管理我们车间的办公室主任。说来可笑,当我拿着装着厚厚的牛皮纸袋纸稿交给办公室主任时(姓刘,大学生),他以为我给他送钱不予接受,因为那个时侯车间正好出了个责任事故,我是上料车间的负责人,他以为我拿钱走门路解决责任的(其实那个车间的领导是表兄郭永旭,天塌下来有大个子,我只是个记录考勤的人),我说:诗稿!那个刘主任才从牛皮纸袋里抽出纸稿(手写稿)细细地读了,“好!好!好!我一定转交编辑!”——他说。九月底刘主任叫我取报纸,还给了一点鼓励费和一些稿纸,因为我是打工的农民工不是本厂职工,几天以后就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厂里俊男倩女争相打听写了《我热爱的扎布耶》的作者(因为这张报纸发诗歌是创刊以来的第一次,并且是行很长的自由诗,让他们惊呆了),也使我着实“自豪”了一把。厂里的工人、领导不再对我们这些农民工(我们上料车间是十个人的班组)哟三喝五指手划脚甚至吹胡子瞪眼睛了,我第一次尝到了“文化”的“甜头”……十月底收秋时节我辞别回家帮助收秋,那年是四女儿蔺蓝天一岁半,我在厂经理“你别回去给我们的厂报当编辑,明年把你招为合同”的承诺中依然决然回到家里……孩子太小,我无法分身;孩子重要,我可以放弃任何机会!有人说过:成功的路不太拥挤,因为坚持下去的人很少!在跟着一个私人老板打工的几年里,更多时侯在县城或县城附近,一次胡走乱转突然发现体育馆楼下有个“桃花山编辑室”的铁牌子,好奇地走进去看个究竟,里面是老人,后来逐渐明白是退休了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编辑,以言谈中发现很多“文化元素”,而且这些老编辑们和蔼可亲、幽默风趣、踏实认真……正好前一年清明节我去过甘肃省会宁县四房吴镇南坡川村(现在归属大房村)所在地的红嘴山,看过埋在山坡的郭富山坟墓,在一个闲得无聊甚至发疯的夜晚“记忆犹新灵感大发”,就凑足了两首《踏访红嘴山》,属于仿古诗(我至今不懂古人平仄的格律框架,认为那种框架把思维和意境束缚的很死,像是绑住四肢还要跳出优美的舞姿一样),就是那种每首八句,每句七个字的方式,也就斗胆把这个诗稿交给《桃花山》的老师,结果一字没变的被刊发了(当然以后发了很多诗歌、散文或者随笔),我认定自己要写或者写好就得给各种报刋杂志投稿(有些稿件编辑还会修改),一则衡量写作的优劣,二则扩大阅读的份量,三则学习编辑的写作技巧……后来把刻意写作的通讯稿《会宁,有片热土叫大沟》(字)以“纪念党庆征文”的要求寄给《白银文学》被刊登了。这种不断被刊登稿件的机遇锻炼了我的胆量,后来细细一想,是那些编辑在鼓励我,既然是鼓励也是一种好事。于是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省报《西部发展报》的记者杨宝国,推荐我给《甘肃科技报》下属的副刊《健康周刊》写稿并成为其报社的“特约记者”。四年来,这种“特约记者”的写作并没改变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命运,倒使我倍感一种社会压力,我只好把这个证件上交给报社,婉言谢绝再次续签合约。从此我便以一个作家的“派头”写起纯文学的作品,比如仿古诗词、自由歌绝、以至散文和小说……只是那时把写成的“作品”给自己发表——即发在自己的QQ空间,向所有读者开放,而需纸质刊登的编辑可在我的空间自由选择(复制)用运,比如甘肃会宁老协的《桃花山》、文联的《会师风》、文化馆的《会宁文化》……等等,后来的后来,有一个杂志的“责任编辑”声称“选我的作品是照顾情面”,这话反而伤了我的“情面”,一种被“瞧不起”的自卑感磬石一样压在心头,然后我想了又想:自己的作品需要照顾刊发,是自己的水平倒退了吗?带着这些疑惑我不再向这些杂志投稿,竟然沉默了两年多时间。还是后来的后来,我把自己的作品以电子版的形式发给一些省、市报纸的编辑,比如《白银日报》《甘肃工人报》《华夏文明导报》……等等,虽然发稿是“沙浪而去犹然金粒可见”的被刊发了几首(篇),我感谢省市报纸编辑对我的“倾情照顾”——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也有资深编辑瞌睡丢盹的时侯;天下之大幸运倒有,也有愣头青子不妨被“幸运之神”碰个满怀……年5月,当我知道“西雁.领袖城旅游”征文时,偷偷的将曾经写过的一篇字的采访专稿《颐馨理念故土情》发过去,然后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半年以后接到电话通知,说是这篇文章获了个优秀奖……说真心话我没有高兴起来,因为获得这个“殊荣”的人永远不属于我,而是一次偶然巧合,会被人怀疑以后诅咒的,什么“别人代写的、转载摘抄的、没有价值的……”等等言论,“佛长千只手按不了众人的口”,况且那些专事诽谤之能事者除了坚守诽谤的“阵营”,要么沉默寡言要么相悖逆论要么轻蔑而视……让我哭着没个好声气!无独有偶,福不双降!年5月,我又发现《文学与艺术》微刊编辑部以“全国首届七夕.华原杯”的“名堂”征文,再一次按挪不住心情,把已经写好的六首“自由诗歌”通过网络以电子版的形式发过去,一月以后通知作品“入围”,再等一月的8月8日说是获奖了通知领奖……份稿件中被选中,我不敢相信,因为我看过每个投稿者的“作者简介”,很多是“中国诗词协会(学会)会员”的知名作家而且著书颇丰,然而我拿到《荣誉证书》以后尽可能管好自己的心——低调!但还是忍不住把照片发在空间“晒”了个不亦乐乎,为什么要彻彻底底的“晒”呢?因为当天夜晚我梦见了故去十年多的父母、因为远在浙江省教书的女儿打电话说梦见她的爷爷奶奶、因为在一个北京什么白癜风医院好北京治疗白癜风的最好医院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2016全国检察机关科技装备展
- 下一篇文章: 父亲的汤瓶那抹沉重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