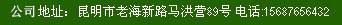|
父亲的汤瓶 文/沙存善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间,父亲过世已快三年了。 父亲对于我们子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父亲去世后,子女们在一起时,谁都不愿主动开口去提说他,或者评价他。父亲是年过世的,活了七十七岁。他在世时,就像河州城里每一个普通的穆斯林成年男子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家务操劳奔波,走完了属于他的那个光阴。 父亲在世时,每逢春节、尔德等节假日,兄弟们总会从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风尘仆仆,赶回河州老家团聚。每次回家,都要按照父亲的“最高指示”,家里一定要请阿訇诵念“亥停”(《古兰经》段落),“亥停”临近念毕,父亲一定要请阿訇为所有家人诵念恕罪的“讨白”(忏悔词),祈求真主恕绕他的家人的罪洐,祈愿儿女们为人处世始终要身怀一个好的“随法提(举念)”。念“亥停”的那两天是“父亲的家”里一年四季最繁忙的日子,也是儿女们一年四季最为幸福惬意的日子,全家老小20余口人齐动员,买羊宰鸡,烧火煮肉,煎油香,做碗菜,那种干家务活争先恐后,喜气洋洋的居家景象将全家人一年的乏困和忧愁扫的一干二净。等到节假日结束,大家准备返回自己的小家时,总会依依不舍,留恋这一年里最开心、愉快的团聚日子。 如今父亲已离我们而去,兄弟们为了各自的生活和工作奔忙,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虽然回家、看望母亲、团聚仍然是大家一年四季最盼望的事,但每次回家,当远远看见夕阳映照下那熟悉的巷道,看着岁月打磨,历经沧桑的院墙和门头,回家的脚步愈发沉重,内心会隐隐发出阵阵欲哭无泪的悲怆,是啊!又回家了,可从巷口再也听不到父亲在庭院里修补汤瓶,铁锤敲打发出的“哒哒”声;从家门口再也听不到父亲那高葫芦大嗓门的谈话声。父亲是他那个家的顶梁柱,他倒下了,这个家就像坍塌了一半,从此,庭院寂静,大家都变得沉默寡语,即便有子女想寻一顿父亲的“骂”,也求之不得了。 环顾老家,庭院依然洁净,湿油油的芍药花低矮着头趴伏在花圃围栏上,仿佛在讲述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是啊!我们的老家已不见了昔日的热火朝天、嬉笑怒骂,一切都已显得那么平淡,只有那尊家传的铁砧在屋沿下风吹雨蚀,依旧发出乌黑的亮光,还有那把父亲亲手铸造的汤瓶孤傲地挺立在堂屋台阶上。今天,老家里已快寻不到父亲当年制作汤瓶的痕迹了,那个曾享誉河州,循化、化隆巴燕戎的铜匠世家,那种曾让全家人赖以活命的汤瓶制作活儿,在现代工艺的吞噬下就这样慢慢断代失传了。 汤瓶,这种只有中国内地回回人如此称谓并使用的盥洗用具,与中国古代汉族家庭曾较长时间使用过的一种洗漱器具执壶极为相似,执壶有金属的、也有陶瓷质的,形制为鼓腹、长颈,带流口,这在今天出土的唐宋金属、陶瓷器中能够看到,尤其是在宋元工笔绘画中可以看到侍女在一旁手端执壶,给主人浇水洗手的情景。世事变迁,祸乱频繁,曾经礼仪化的考究生活在今天许多汉族家庭中已不复传承,大小便后及饭前洗手等优良的卫生习俗似乎已坚守得不那么普遍和严格了,形似汤瓶的执壶早已从汉族家庭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回族的汤瓶,还像维吾尔、哈萨克等突厥民族使用的萨玛瓦尔,只是萨玛瓦尔基本用新疆本地红铜铸造,材质柔软,脖颈细长,壶身錾满他们喜闻乐见的花卉、几何图案,萨玛瓦尔放置在地上,整个器型好像一只束翅挺立的鹰隼,流口极像鹰隼利嘴。 “回回家里三件宝,汤瓶、吊罐、白号帽”,汤瓶是回族家庭独有的家当,她是世俗的,又是神圣的,她伴随着每一个回族人呱呱坠地直至离开这个世界,回族人用一壶壶流动的净水清心净体,洗涤去身体和精神的污垢,回归生命的本源。按照教法,回族人礼拜、房事、月经、产后必须要用汤瓶做大、小净,亡故要用汤瓶为亡者“抓水”(洗大净)。回族经营的茶馆、餐馆门口都要备有汤瓶,供洗漱和洗小净之用。华北、东北的回民餐馆还喜欢把汤瓶造型刻画在餐馆的招牌上,作为醒目的“清真”标示。所以,汤瓶对于回族而言,除了她的世俗功能,其实还是一种载道之器。 快20多年了,我情有独钟,遍访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民族博物馆,处处找寻回族汤瓶的踪影。我目睹了许多材质、形制各异,被称之为民族文物的“汤瓶”,她们收藏展示在展柜里,材质有铜、铁、锡、搪瓷、砂坩泥,铝、塑料等不一而足。年盛夏,我在民国时期著名回族教育家马邻翼的家乡湖南邵阳市清真南寺回族博物馆,看到了两把就地取材,朴实无华的竹筒制汤瓶;我曾在青海民族大学文物陈列馆看到过一把古拙的木头凿制汤瓶;在西藏拉萨看到过藏回使用形似藏式奶茶壶的汤瓶。目睹这一把把具有传奇色彩的汤瓶,聆听各地穆斯林讲述汤瓶的故事,我心潮涌动、悲喜交加,倍加怀念我们那个匠人世家曾经的辉煌,时时勾想起父亲一辈子割舍不弃的汤瓶情节! 在古城临夏,我们沙姓家族没有正式修编的家谱,家族源渊基本靠口头传述。据对临夏沙姓家族的考察,当地沙姓家族主要有4支,但相互之间没有亲缘关系。我们这一支沙姓家族据先辈们讲,源自陕西西安广德门,太爷辈时迁徙至甘肃巩昌县,即今天甘肃陇西县。当时太爷有六个儿子,2个女儿,到达巩昌时因家境窘迫,将老二、老四儿子过继给了巩昌县当地的一位回族马姓太爷,两个儿子也就随了马姓。所以我们家族在临夏被称为“沙马家”,沙、马虽为两姓,但实为一家。太爷是旧社会河州地方很有名的金匠,手镯、戒指、脖链、藏饰金银活儿样样精通,河州八坊的人都称呼太爷为“巩昌阿爷”。 仔细分析先辈们的传述发现,我们这个家族并不是河州本地的原住民,在河州四乡没有耕地,是典型的城市手工业家庭,极有可能是清朝同治回民起义(至年)时期,随白彦虎起义大军从陕西西安广德门一带流落到今天陇西县,后又辗转定居河州的。 我们的本家爷爷是年过世的,享年64岁。他的铜匠铺在今天临夏市北大街西端红水河桥头边上,是个两层土木结构的连家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临夏八坊、青海同仁、化隆巴燕戎、循化的老人们还都称呼他“铜匠阿爷”。爷爷集铜匠、金匠、铁匠于一身,锁钥、门扣、炒锅、藏刀、水桶样样都能制作,能说一口地道的安多藏语,化隆、循化许多黄教寺院屋顶宝瓶上的髹金是专门请他做的。爷爷的匠人活儿虽然做的很多,但做的最多最好的还是他用黄铜、红铜打制的汤瓶。他做的那种大肚子、长脖颈铜汤瓶,锤子锤,焊药焊,整体岑光发亮,真舍不得拿去火上烤,炕里煨。在生活异常艰辛、信仰底线都确保不了的岁月,爷爷的铜汤瓶浇灌着他那一大家口子人生活的希望,也悄悄满足着临夏四乡穆斯林信仰和生活的需要。 年爷爷去世,匠人的衣钵传到了父亲手里。那时,第一机械工业部刚刚将上海电影机械设计研究所整体搬迁到临夏,改名为一机部临夏电影机械研究所,在临夏建立了甘肃光学仪器总厂。甘光厂生产的光学镜头和放映设备用料主要是铝材,镜头先由翻砂工铸造,再由车床工后期制作。甘光厂的到来给偏僻闭塞的河湟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工作生活理念和工业技术,对临夏地区古老的手工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年的临夏,正处在极左路线横行猖獗的时期,社会凋敝,民不聊生,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斥着饥饿和焦灼的面孔。那时,父亲刚从甘南迭部林场病退回来,家里生活到了揭不开的境地。但是,失望的尽头总能看到希望的光亮,一位热心肠的临夏汉族翻砂师傅“王大嘴”出现了。至今我还记得他清朗的身影,30岁左右,一张大嘴,脸色白皙,身材消瘦,穿一身蓝色军便装。我一直在揣测,他极有可能是甘光厂就地地招录的一名翻砂工。大概是在年的一个春节,他开始在我们租住的小土棚房里,手把手给父亲传授起翻砂和铝材熔炼技术。日复一日,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铝材汤瓶的铸造终于成功了,我们一家7口人赖以存活的手艺终于学到手了。“荒月里饿不死手艺人”,从此,我们的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手工业家庭,史无先例的铝材翻砂汤瓶在临夏四乡穆斯林家庭中开始悄悄使用了。 养家糊口的手艺学到手了,但是,铝材汤瓶从制作到出售,每天都面临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风险。制作初期,因为工艺不熟练,一天只能铸造2—3把汤瓶,两年后慢慢增加到8把左右。那时汤瓶铸造就像偷鸡摸狗,危机四伏。为了躲避居委会、市场管委会人员发现抓捕,熔炼和铸造的时间一般都在早晨6点之前和晚上9点以后进行,真可谓鬼鬼祟祟,干着见不得天日的事情。成品做出来后,如何安全卖到买主手里又成了一大难事。那是“文革”肆虐的特殊时代,一把汤瓶仅卖1元2角钱左右,但钱很值贵,买一对汤瓶对一般穆斯林家庭来说,的确是一笔大的开支。多少父母省吃俭用,分分钱、毛毛钱地打凑着,待姑娘出嫁时买一对红头绳系着瓶盖和瓶把、银光闪闪的铝材汤瓶作陪嫁。 当中国传统主体文化都被当做封建反动垃圾横扫出门时,相对异质的伊斯兰文化信仰自然在劫难逃。到年粉碎“四人帮”时,临夏全州的清真寺、拱北被拆毁殆尽,个人和家庭宗教活动被严格禁止。不仅如此,城郊的穆斯林农户被强令养猪。记得我们家的穆斯林邻居是城关公社肖家大队的农户,按照公社“猪的浑身都是宝”的指令,在自家院墙通道里搭盖了猪圈,喂养着好几头猪,家人因犯忌讳,猪圈门很少打开,喂养基本是用铲子隔墙撩食,育肥效果极差。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邻居家猪圈门没关好,一只小猪崽“嗷嗷”嚎叫奔窜到了我们家的院子,大家惊慌失措,躲避不及。 封斋、煎炸油香是严格禁止的。斋月凌晨3、4点钟,居委会主任经常带领工作队挨家挨户检查,看见那家的煤油灯还在忽闪发亮,就会破门而入登记、训斥,第二天早上,还要头带报纸做的大高帽沿街游行。那时候,临夏八坊居民因公职人员少,加上禁止从事个体生产经营活动,闲散人员集聚,成年人无工可务,过着面面相觑,百无聊赖的赤贫生活。生存是人的第一需求,在绝对贫困状态下,一些回族姑娘上街时被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一带来的蒙古族青年搭讪悄悄领走,她们就这样嫁为人妻,生儿育女,跟随了蒙古族的生活习俗。年的冬天,灾难也终于降临到了我们家里,不知谁人举报,临夏市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人员突然来到我们家里搜查,惊慌失措的父母赶紧往麦草堆、土坯墙槽里藏匿制作汤瓶的翻砂模具、矬子等。但为时已晚,所有的制作工具被清查出来。当天,父母两人被强令手拎翻砂模具和半成品的汤瓶沿街游行,以示警戒,市管会还没收了所有制作工具,母亲被强制参加街道办事处举办的思想改造学习班,直至年粉碎”四人帮”。 年,随着极左路线的逐步终结,父亲汤瓶制作的春天终于到来了。那时,兄弟们已渐渐长大,能给父母帮忙顶住点事了,汤瓶制作最好的月份已能达到80多把,汤瓶的价格也上升到每把2元5角钱。城乡商贸市场逐渐开放,父亲的汤瓶除销售临夏四乡外、还有兰州、西宁、固原、新疆的商户也来家里取货,家庭的贫困面貌逐年得到改善。今天细细算来,从年到年的26年间,父母和两个帮工兄弟大约制作了近4万把铝材汤瓶。凭借着汤瓶制作带来的恩典,我们兄弟五人先后完成了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其中3人被录取到省城高等院校,接受了大学本、专科教育。 现代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传统手工业为代价的。从战国时期到今天,中国金属器的铸造基本采用翻砂浇铸法和失蜡法,几千年如一日。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科学春天”的到来,铸造锻造工艺发展更新,钢制模具、电溶解技术、塑料压模技术被不断吸收到民间手工业领域,也应用到了汤瓶制作工艺中。铜材、铝材汤瓶实现了批量生产,塑料汤瓶物美价廉,更受城市穆斯林的青睐,世代传承的匠人世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汤瓶制作成本和卖价出现倒挂。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传统个体手工业必须面临的残酷现世!对父亲来说,不进行技术转型,就无法继续靠此为生。 但是,父亲老了,他的汤瓶制作观念深植于他的思维模式,我们无法勉强。况且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走上了各自全新的工作岗位,父亲的汤瓶,已后继无人。 年,说来极其巧合,在这个20世纪即将结束的特殊年份,那个曾给我们这个苦难家庭带来无限恩典、也惠及河湟穆斯林家庭的汤瓶制作活儿悄然停止了。21世纪,已不是父亲他们这辈人能够诠释的故事! 我们的祖辈与汉、藏民族有着极其深厚的世交关系,生产生活相互依靠,不离不弃,对各自信仰和习俗的尊重发自内心,从不感到对方是另类或是社会竞争的对手。逢年过节,相互之间一定要串门祝贺,交往中丝毫不掺杂民族优越和利己的思想,那种人与人之间真实无妄,朴素无华的相处之美,让今天那些著述等身、具有民族偏执思维的专家学者无地自容。在“民族国家”这些概念还没有被西方东方学家制造出来的时候,人类的迁徙权与生存权、发展权紧密相连,世界民族的大流动、大迁徙曾经那么激越地互动着,种族的迁徙、交融进行得那么酣畅淋漓。人类从不像今天这样,以国家、民族为徽标,画地为牢。 汤瓶,作为中国回族穆斯林和清真的标志,从形制到内容,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极其自觉的融会,是回族浸淫中华文化数千年,早已完成中国本土化的见证。 汤瓶,你用洁净之水复苏了多少无望者的心,你用晶莹剔透温润了多少离乡人的情,你用圣洁的甘露浇灌出多少信仰的花。 好男子出门一把壶,任凭天南海北、刀山火海,也能蹚出一条俊美通达的路! 到如今,父亲的汤瓶是一种怅惘、忧伤,更是我们儿女们引以为荣的的思念、忆想……,激励我们完成父辈们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望! “河州文艺”白癜风怎样能治好白殿疯病那家医院看的好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我的文化之路
- 下一篇文章: 甘肃建成全国第一个农村饮水安全到户到工